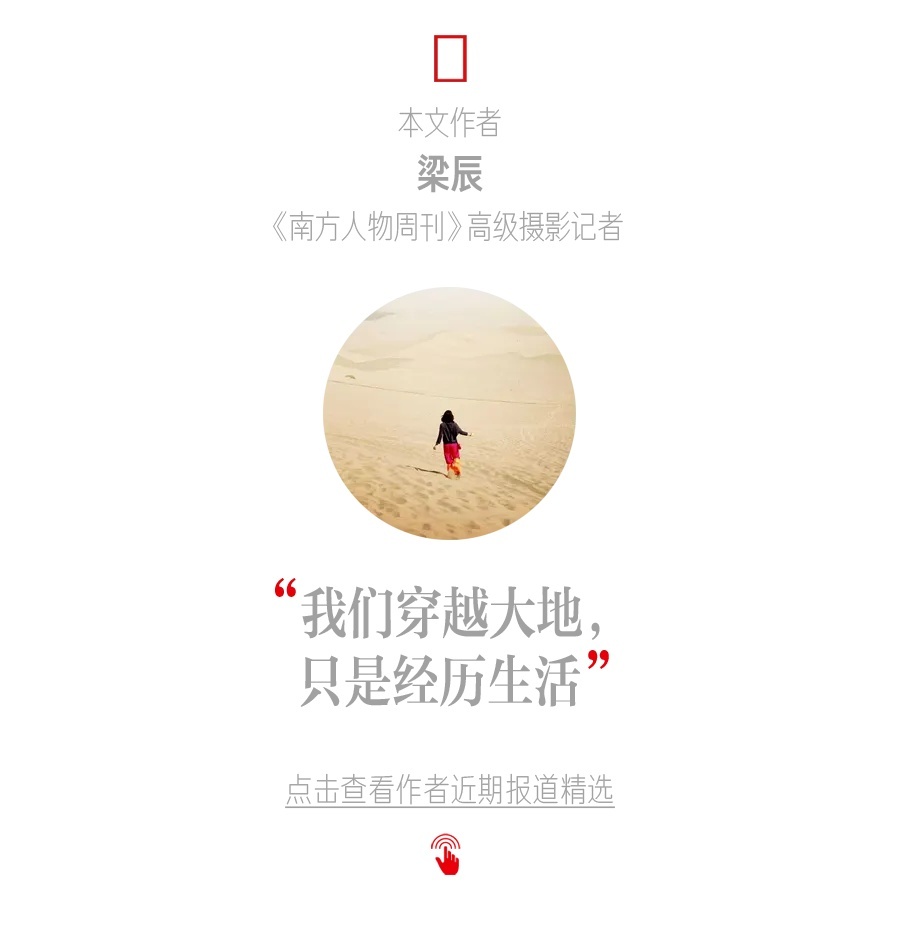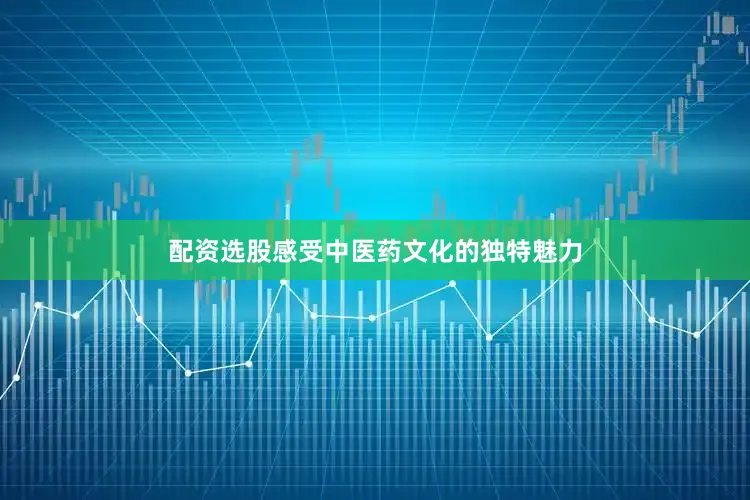▲一位来京出差的住客租住在一家青旅的单间 本刊记者 梁辰
“对北京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感觉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标题来自图片故事《住在青旅的年轻人》留言区里对受访者阿扎“北漂”经历的一条评论。
暮春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家青旅遇到了这位22岁的藏族小伙。夕阳挂在楼群间,泛着橘红的光,他和刚结识的舍友正在露台聊天,欢快的谈笑声在空气中跳跃。
阿扎的“北漂”经历却没有这么轻松。据他讲,一年前他揣着600元从老家甘肃甘南来到北京。面对陌生的环境加上普通话不标准,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只能找些日结的零活儿。钱包很快见底,阿扎经常就近睡在某个居民楼的楼道或者公园,他说每晚睡觉时他会把双手交叉护住胸前的内兜,那里有身上最值钱的物件——手机和钱包。
后来,某次露宿街头时,阿扎遇到了一位“贵人”大哥,介绍他去夜店当保安,这才有了稳定的工作。因为“干活卖力又踏实”和外向的性格,他的月薪从最初的四五千涨到六七千,好的时候能达到“1个w”,相当一部分花在食宿和喝酒上。
那天聊完,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面馆吃饭,阿扎熟练地蹬上共享单车,随口说了一句,“我最擅长的还是骑马。”在家乡甘南,他从小就跟着家人骑马放牧。
在青旅经常会遇到像阿扎这样有故事的年轻人,“临时感”和“过渡期”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有多“临时”?入住的时限可以是“三个月的工作试用期”、“等下周面试结果出来”或是“下午如果再借不到钱(交房费),就直接坐火车回家”。
大多数受访者对“过渡期”的现状持保留态度——聊聊经历可以(刊发报道时要化名),但拍照免谈。操作这个选题期间,我加了26位住客的微信(不算小红书上“打招呼”的私信),只有极少数同意接受采访和拍摄。
一位从外地来京走秀的模特,本来已经同意了,也很配合地协助我拍摄秀场内外,但一提到记录在青旅内的生活场景就一再推辞,最终以“不想抛头露面”为由拒绝授权刊发照片。换位思考一下,我也可以理解,只是可惜了那些五光十色的秀场照片。
住客这边推进困难,只能寄希望于经营者。我通过多家在线旅游服务平台搜索“青年旅舍”,一家家打电话询问。“礼貌”的回应是被挂断电话,有些旅店在不同平台、以不同名称和电话登记,当重复接听到我的来电时,难免出言不逊。
最终,一对来自山西的夫妇接受了我的采访请求,并热心地帮我联系住客,才促成了这篇报道顺利完成,也让我切身体会到“记者这个职业就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
阿扎的故事还没结束。报道发表后,他邀请我和那天一起聊天的舍友(已经搬离青旅)去一家“超好吃的火锅店”,但因时间凑不上,没有成行。后来,他说自己搬到了“消费低一点”的马驹桥,因为“身体熬不住了”——在采访中,他曾提到做保安长时间昼夜颠倒和高分贝噪音的工作环境让他的身体吃不消。“找不到工作,有点落魄,但没有颓废,每天都在找。”再后来,他曾向我借过两次钱救急(充话费和“吃个饭”),数额不多。
阿扎起伏跌宕的生活超出了我的经验和想象,有时甚至对某些细节充满疑惑,却又无从考证。最近一次联系,他直接发来正在医院输液的照片,“你看我现在在干嘛。实在熬不住,回老家啦.......”
至于对大城市的幻想,“也许过段时间再回去吧,但也不想回去。对北京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感觉了。”(详见相关报道《住在青旅的年轻人》)
蜀商证券-配资网站-配资点评网-我要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